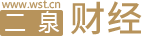现代金融市场是一个以银行为核心的信用货币体系。从近现代史的发展来看,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银行,从民主国家到威权国家,概莫能例外。最有趣的例子当属哥斯达黎加和科威特——前者没有军队,后者不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许银行。
为什么银行会对国家如此重要,甚至比军队和税收的存在更普遍呢?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作为一种组织形式,银行和欧洲大规模的民族国家是在16-17世纪左右共同演进的。著名学者哈伯和凯罗米里斯所说的“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1]。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和“银行”是怎么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
一、银行与欧洲“国家”的同步演化
如果有个月光宝盒,让我们回500年前的欧洲,我们看到的会是《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场景:
16世纪之前的欧洲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封建制度”。中世纪的欧洲散落着和成千上万和临冬城的史塔克家族一样的贵族领主,他们统治着小块土地,以城堡来保卫领土,领土的产出盈余维持城堡的臣民和军队。慢慢的,随着实力的变化,一些大的,有能力的统治者产生了向外扩张的欲望,但是要在对手林立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可以持续扩张的贸易网络;第二,要有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

在实力相对均衡的欧洲,满足要上面这两个条件都需要金融家进行撮合:远洋贸易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的实体(e.g.,国家)来捍卫他们日益扩大的贸易航线,执行日益复杂的合同;统治者则急于扩大版图,也需要商人们建立商业网络,来加强自己和各国之间的联系,以及维持海外帝国的运行。不管是贸易还是版图扩张,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金融家充当了这个角色,他们创造了汇票,本票,清算,融资这些金融工具,为商人提供了一个高效的管理远程贸易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统治者提供源源不断战争资金,也从统治者手中取得特许权力,获取垄断收益。这样一来,商人,统治者,和金融家这三个群体的目标通过银行被结合在了一起。尤其到了16世纪之后,指南针,火炮,大帆船,望远镜等技术,还有天文地理知识都取得重大突破,人类的航海能力和战斗力有了巨大提高,全球范围的征服和贸易都成为可能。在各种金融创新(e.g. 国债,股份制公司,特许银行等等)的支持下,远洋贸易,国家征服,和银行业开始互相交错影响地共同演进,没有银行的巨大助力,当时并不算强大的欧洲统治者们很难完成在以民族国家的身分,进行全球征服的事业。

有两个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三者中间的关系:荷兰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它吸取了威尼斯国有特许银行的经验,尽量连接全欧洲的银行帐户所有者,为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提供专门的票据清算,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全球票据结算中心。这个银行推动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为荷兰在17世纪建立的海上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一个例子是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特许的股份制银行,英国政府赋予了这家银行垄断发行银行券的权力和各种税收优惠,使得它能获得长期得,低成本的资金,作为交换,英格兰银行要为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战争融资。这一设计使得英国政府拥有了稳定的可靠的战争资金来源,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英格兰银行是英国18世纪后在海陆两地战胜各种对手,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武器。在贸易与战争的硝烟中,银行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共同演进成了“现代欧洲”的模样。这个模式随着“五月花”传到美洲大陆,又开启了另外一个金融的美利坚世纪。
二、国家塑造现代银行职能
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和民族国家的日益强大,国家内部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维持政治秩序的需求,借鉴了英格兰银行和威尔瑟银行等先驱的经验,各个国家统治者发掘了特许银行更多的职能,比如支持战略重要行业的发展,通过货币发行控制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对居民施行后住房和其他福利补贴等等。从19世纪开始,国家学会了通过银行调动大规模的资金,用来服务于新兴的国内政治利益,这一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和关键。
可以说,特许银行的创立是起源于现代欧洲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它催生了很多根本性的金融和政治创新,包括法定货币(纸币),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等等。
比如说银行券的发明,不但解决了金属货币流通不便的问题,更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依靠的是运营者的信用。政府特许的银行券(e.g.,法定货币,美元,人民币,英镑),则使得这个价值标准与国家信用被绑定在一起,催生了国家信用膨胀的新时代。(“银行货币”是构造现代信用社会的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金融行为都是基于这一创新)

除了银行券以外,在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发现,对国家概念的接受程度是社会动员的最佳利器,而在欧洲这么一个分崩离析了上千年的地方,“国家”的概念非常淡漠,要塑造民族国家概念,需要给“人民”以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进行刺激,这个时候,“公民”就开始有了和“国家”议价的能力,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大为拓展,自然也就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充分就业,提供社会保障,为个人提供信贷流动性——从19世纪开始,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就一直想办法为商人,农民,购房者提供信贷;德国总理俾斯麦则要求银行体系为德国的钢铁,化工,电力等产业提供大量融资,同时要求证券市场在养老金,公共医疗,失业救助等方面提供大量支持——“国家”的宏大目标需要庞大的稳定的资金支持,而银行体系,毋庸置疑,提供了最优的途径。在历史的演化中,商业银行体系和国家能力藤蔓交织,银行体系成为了国家和政府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途径。国家特许经营下的银行与政府政策相融合,它不仅是经济工具,也是政府控制社会秩序的机制。

所以在现代世界里,银行是比军队和税收更普遍的存在。 因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演化是依赖于统治者,商人,和银行家之间的伙伴关系。统治者需要商人构建商业网络,从而将整个国家黏合在一起。商人需要统治者提升实力,捍卫远洋贸易路线,保证合同强制执行。商人和统治者都需要银行家,统治者需要为战争进行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融资,商人需要银行家创新金融工具,提供远洋贸易的金融服务。这三者之间通过特许银行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金融,政治工具得到了整合。在分权制衡的欧洲, 银行创造了国家,国家也塑造了银行。
[1] 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金融制度学和金融史是其专长,史蒂芬·哈伯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对产权有长期的研究。这句话本来是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发动了战争”,他们俩在其合著的《人为制造的脆弱性》一书中,改成了“国家创造了银行,银行创造了国家”。
来源于格隆汇